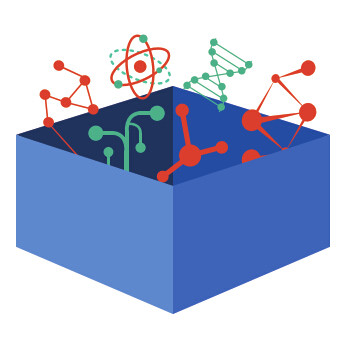身处异乡,难免会起莼鲈之思。
每年开春,最令我魂牵梦萦的,是家乡的野菜。苏轼的《浣溪沙》中有道:“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蓼、蒿皆为初春南方的乡间野菜,此外还有荠菜、水芹、草头、菊花脑、豌豆尖、马兰头等,都是刻在江南人基因里最质朴的珍馐。冬去春来,山麓田畔的野菜尽显生机,头茬的野菜鲜嫩清新,自带芬芳,即便是裹着泥腥味的苦涩都充满了灵性。

儿时每年清明前,父亲会开车带上一大家子人去郊外踏青,挖野荠菜、摸螺蛳是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欢乐。母亲除了用野荠菜做肉馅馄饨和豆腐羹外,还经常炒一道荠菜年糕。初春的野荠菜肥美多汁,鲜嫩无比,略带毛糙的口感与软糯润滑的水磨年糕彼此成就,只需在锅中加些猪油和盐,翻炒几下,便能激活香气,若是再添入些清雅隽永的春笋,如此一盘春意,更是妙得直击心扉。

南方人都喜欢吃年糕,江南人的春天绕不开各种野菜炒年糕。除荠菜外,草头炒年糕、马兰头炒年糕、韭黄炒年糕也各有滋味。年糕肌骨莹润,洁白丰盈,与清新灵动的野菜相互纠缠,一青一白,原汁原味,即便没有肉类点缀,也鲜美无比。
草头炒年糕也是江南的吃法。吃草头要赶早,春节过后,下过霜的草头特别嫩,炒年糕时先把锅里的油温烧高后再下草头,和年糕快速翻炒,时间不宜太久,否则口感会老,用少许白胡椒和几滴白酒增香提鲜,是这道菜的灵魂操作。
我在北京,春天买不到南方的野菜,就会用香椿替代,做一盘香椿炒年糕,炒时往里头丢入些开洋,滋味便鲜香浓厚。香椿本是盛行于北方的野菜,是香椿树的嫩芽,早年我从梁实秋的文字里读到它,八年前到北京才第一次尝得。现在上海的菜场和超市里也能买到香椿,父亲的朋友在崇明有一片用来种时令蔬菜的地,父亲说,朋友每年一给他送去香椿,他便知春日已至。香椿这种野菜绿中带红,取最嫩的部分,用沸水一焯,剁碎,可凉拌豆腐或炒鸡蛋,口感像泡开后的茶叶,很多人不喜欢它的味道,我倒不厌恶,觉得它灵动又耐人寻味。
除了家乡的野菜,春日的河海湖鲜也总能令身处北京的江南人燃起思乡之情。苏州吴江自古就有厚重的渔文化,鲈鱼、“太湖三白”、螺蛳、蛏子都是水中的初春恩物。苏州人吃鱼也最讲究时节,在民间流传的谣谚中提到:正月塘鳢鱼,二月鳜鱼,三月甲鱼,四月鲥鱼……
塘鳢鱼是苏州人眼里的春日第一鲜。这种鱼个头如巴掌小,长得其貌不扬,有些小家子气,却肉质松嫩,味道鲜美,用它炖蛋、红烧、糖醋、糟熘,或者用塘鳢鱼片炒荠菜末,都是美味。很多年前,我在上海青浦的农家乐吃到过莼菜汆烫鱼片,至今念念不忘。莼菜清脆爽滑,最让我迷恋的还是它表面自带的胶质物,让鱼羹变得香稠。
相比之下,鲥鱼天生自带雍容华贵的气质,古人赋予它典雅清高的品性。张爱玲也说人生有三大恨事:“一恨鲥鱼多刺,二恨海棠无香,三恨《红楼梦》未完。”鲥鱼丰腴鲜美,足以掩盖它多刺的缺点。清蒸鲥鱼是最经典的吃法,用早春的嫩笋尖和几片南风肉相佐,三鲜相撞,风味绝妙。鲥鱼最精华的部位无疑在鱼鳞,银白色的鱼鳞只需轻轻用勺子一刮,便能整片地脱落,吸饱鲜味的鳞片带着丰腴肥美的膏脂,咀嚼时口感酥脆又绵软。
清明节前的江刀鱼最值得让人特地跑一趟江苏。有一年的3月份,闺蜜从老家启东给我冷链邮寄了两条品相极佳的江刀到北京,真是解了我很久未被满足的口腹之欲。新鲜的刀鱼无需用葱姜去腥,只需加点猪油蒸一下,那滋味就“鲜得掉眉毛”。刀鱼馄饨是最近这些年流行起来的,窃以为是把品相一般甚至下乘的刀鱼搅成泥与猪肉混合做馅,包成馄饨,价格确实亲民不少。一到开春,许多老上海人都要排队去福州路的“老半斋”吃一碗刀鱼汁面和刀鱼馄饨。

江南人的食味知春,食的是来自乡间的野菜和湖河的鱼鲜,这些时不待人的鲜物如妙龄少女般,无需添施粉黛就能尽显本味,当市场上见不到它们的时候,便知道春天过去了。